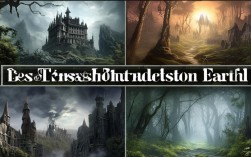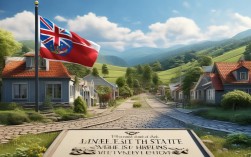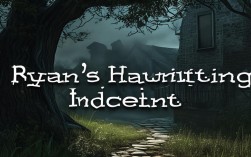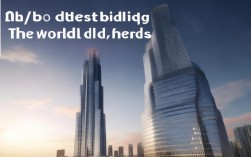流星,这一夜空中瞬间划过的璀璨光迹,自古以来便吸引着人类的目光,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古代,人们将其视为天意的征兆,敬畏地记录下每一次“星坠”的景象,而世界上最早关于流星的系统性文字记载,并非出现在其他古文明,而是源于中国商代的甲骨文,这一发现不仅改写了天文学史,更彰显了中华文明对自然现象的早期关注与记录传统。

商代晚期(约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),中原地区的先民已掌握成熟的占卜文化,他们将龟甲或兽骨经过整治,在表面钻凿出细密的坑槽,再用火灼烧,根据裂纹的走向解读“神意”,并将占卜内容契刻在甲骨上,这些被埋藏三千多年的“档案”,直至1899年才在河南安阳殷墟被重新发现,其中便包含大量关于天象的记录,而流星现象正是重要组成部分。
在已出土的甲骨文中,与“星”相关的契辞超过千条,其中明确描述流星现象的记载有多处。《甲骨文合集》第13443片记载:“癸卯卜,今日雨?夕卜,今日星”(癸卯日占卜,今天会下雨?夜晚占卜,今晚有流星);第11506片则更为具体:“贞,星率西”(占卜:流星向西方坠落),这里的“星”并非指恒星或行星,而是特指“流星”——因流星体高速闯入地球大气层,与空气摩擦燃烧形成的发光现象。“率”字在甲骨文中意为“跟随”或“坠落”,结合“西”这一方位,生动记录了流星划过夜空的运动轨迹与方向,这些记载并非神话传说,而是商代占官对实际天象的观测记录,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
为何商代甲骨文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流星记载?这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独特发展路径密切相关,与其他文明将天象观测权垄断于祭司阶层不同,中国自商代起便形成了“观乎天文,以察时变”的传统,统治者将天象视为“天命”的直接体现,因此对日月星辰的运行、异常天象的出现均进行详细记录,甲骨文作为当时官方的“档案库”,其记载的真实性与系统性远超后世追述的神话或史诗,成为研究古代天象的“第一手资料”。

对比其他古文明的早期记录,这一“最早”的地位尤为凸显,古巴比伦的《天文日记》(约公元前8世纪)中虽有流星记载,但时间晚于商代甲骨文;古埃及的纸草文献(约公元前7世纪)对“火流星”的描述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,缺乏具体的时间与方位记录;古希腊学者如亚里士多德(公元前4世纪)对流星的解释则停留在哲学思辨层面,而非直接观测记录,商代甲骨文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流星文字记载,更是人类用科学态度(尽管夹杂占卜)记录天象的开端。
这些三千多年前的记录,不仅让我们窥见古人对自然的敬畏,更揭示了中华文明在天文学领域的早期成就,商代占官通过长期观测,已能区分流星与恒星的差异,并记录其出现时间、方位、运动方向等细节,为后世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,正如现代天文学家所言:“甲骨文中的星象记录,是中国献给世界文明的一份厚礼,它让我们得以触摸到人类探索宇宙的最初足迹。”
相关问答FAQs
Q1:商代甲骨文中的“星”是否确实指流星?如何排除其他天象的可能性?
A:甲骨文中的“星”需结合上下文与契辞特征判断,在明确记载“星率西”“星陨于东方”等动态描述时,“率”“陨”等动词指向“坠落”或“划过”的瞬间现象,与恒星(位置固定)、行星(运动缓慢)的特征明显不同,甲骨文中记录“星”出现时常伴随“雨”“风”等气象现象,说明其被视为“异常天象”,这与流星短暂、突发的特性一致,现代甲骨学者通过对比后世文献(如《诗经》《春秋》中关于流星的记载),已确认契辞中的“星”确指流星。

Q2:除了流星,甲骨文中还有哪些天象记录?这些记录有何科学意义?
A:甲骨文中天象记录极为丰富,包括日食、月食、新星(超新星)、彗星、太阳黑子等。《甲骨文合集》第11506片记载“七日己巳夕,有新大星并火”,描述了公元前14世纪一次超新星爆发;“癸酉贞,日有食”则记录了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一次日食,这些记录是世界上最早、最系统的天象观测数据,为现代天文学研究古代宇宙事件(如超新星爆发年代、地球自转变化)提供了珍贵依据,也证明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连续性与先进性。